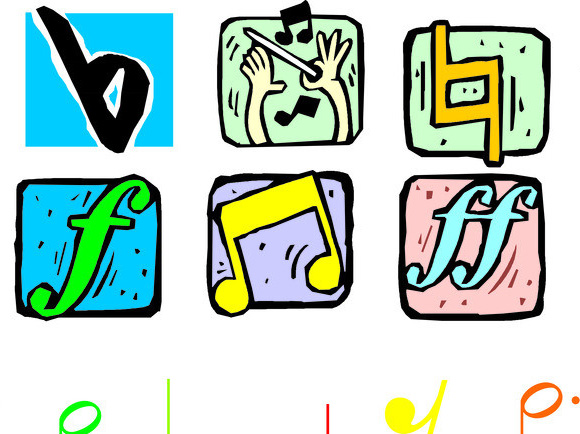
当前,音乐艺术的“生态方式”与其他艺术品种相比似有很大不同:无论文学、美术、戏剧,或是影视、舞蹈、摄影,举凡几乎所有的艺术类型,其主要的活力推动主要是来自最新的创作,而不是原有的经典遗存以及对这些经典的再诠释。然而,自20世纪以降百余年来,现当代社会中音乐生活的主要内容却不再是新出现的作品,而是已有老作品的不断“翻唱”、“翻奏”和“翻演”——君不见,常规音乐会及歌剧院中的曲(剧)目安排,唱片公司新发行的音像制品,以及各类媒体中的宣传报道等,大多以演奏、演唱十八九世纪的著名作曲家的经典名作为主——甚至,大家关注的重心已不再是作品本身,而是具体表演家针对这些经典作品的独特诠释和不同版本。针对这种状况,虽不断有各种异议和反对声音出现,但音乐生活在全世界的这种“厚古薄今”的生态惯性尚未见扭转之势。
在世界各大歌剧院的常演剧目中,一般公认,普契尼(1858-1924)和理查·施特劳斯(1864-1949)是进入稳定保留库存的最后两位作曲家,而他们俩人的创作路径恰恰是传统的调性语言取向,而不是以所谓“创新”见长。现当代的知名作曲家,如20世纪的“三巨头”勋伯格(1874-1951)、巴托克(1881-1945)与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在专业“学院”中享有盛名,但对于普通乐迷和一般听众,他们的作品依然处于音乐经验的边缘地带。至于更近一些的重要作曲家,如刚刚过世不久的德国作曲家汉斯·亨策(1926-2012)和美国作曲家埃利奥特·卡特(1908-2012),以及仍然在世的俄罗斯杰出女作曲家索菲娅·古拜杜丽娜(1931-),恕笔者直言,至少对于国内文化界,他(她)们的大名及其作品的“知晓度”恐怕仅限于作曲、理论界的小圈子。说到国内情况,由于“艺术音乐”的传统积淀和文化积累在中国本来即显薄弱,现当代音乐的生存土壤和生态状况比国外更不容乐观。20世纪以来诸多西方现当代音乐杰作至今仍难得在音乐会上与中国听众见面,而中国现当代作曲家的最新创作至多只是日常音乐生活中的点缀而不是“正餐”。在这样的局势中,对于如“上海之春”这种始终以推出“新人新作”作为核心办节宗旨的音乐节而论,进而对于整个中国音乐界和关心中国音乐未来走向的有心人而言,如何面对音乐创作与社会认可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何认识纠结其中的相关问题,看来确乎是一种不易应答而又难以回避的挑战。
一门艺术的生存状态中,新创作不再居于中心而是滑向边缘,旧有经典反倒是醒目地占据注意力的中心——不妨暂且将这种状态称为“博物馆化”现象。音乐艺术的“博物馆化”现象起于何时,以及这种现象背后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文化根源,本文不拟也无法在此详述。但显然,一门艺术保持活力的主导驱动力理应来自新创作,反其道而行的“博物馆化”生态其实是一种异常,而非正常——音乐艺术“危机”之存在看来已经确凿,不论是否得到公开承认,还是心照不宣。而且,这种“危机”具有全球蔓延性,当然在国内的表现还带着独有的“中国特色”。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人责怪听众的耳朵和头脑过于保守,没能敞开胸怀来拥抱新鲜事物。也有人指出,流行音乐的感官吸引力和触及当下生活的直接性争夺了听者的份额比例,严肃艺术音乐特别是现当代音乐注定只能是“小众”之乐。更有人站在普通听者的立场上反驳说,一般公众无暇也无力跟随作曲家在音乐语言和音响风格上的极端探索或个性试验,因而他们在面对自己“听不懂”或觉得“不好听”的新创作时,自然会选择逃避或忽略——表象之一即是热衷或甚黏附于古典、浪漫时期经典作品的各类不同表演版本,从中获取审美满足。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早期音乐复兴”及“历史本真表演”运动,更是提供了巴洛克时代及以前(文艺复兴乃至中世纪)音乐的丰富宝藏,这些“重新复活”的古乐也成为逃避现当代音乐的又一个“多元文化”选择。具体到中国自身的音乐生态,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状况(诸如艺术音乐传统相对单薄,但民间音乐资源丰厚,20世纪以来音乐的发展又受到强烈意识形态“政统”的左右和影响等等),国人中一般公众(甚至也包括相当数量的专业音乐从业者)回避乃至拒绝现当代音乐的现实恐怕也是在情理之中。
如果说普通听众可以采取回避或忽略态度,专业音乐家和负责任的文化工作者却必须直面这一危机,并思考应对的方略。笔者不自量力,在此提出一些初步浅见——或许这些看法过于理想主义,过于“书生意气”,但只要引发大家对这一危机的关注并引起进一步的反思,本文即已达到目的。 可以分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设法改善我们已身处其中的音乐生态。其一,涉及创作者层面。古往今来,尤其自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性”社会启动以降,作曲家通过音乐语言的拓展,不断开掘出新的音乐表现疆域,从而推动音乐艺术向前迈进。创新和探索于是成为音乐创作理所当然的至高美学准绳。这一美学惯性至20世纪终于达至极端:它表现为作曲家抛弃“共性写作”,不再使用“公共语言”进行表达,而是转向创造各自的“私人语言”——在创造语言之后,方能使用语言。它带来的益处是,创作和表达的彻底个性化;但这类“私人语言”的副作用是,它的“意义共享”程度大大降低,因此普通听众开始抱怨“听不懂”或“不好听”。更加危险的是,在某些作曲家殚精竭虑构造自己的语言体系时,恰恰忽略了要表达的是什么。于是,我们在现当代音乐新作中常常会听到“没有原因的音响”,或是发现这些新作中充斥着“为了声音的声音”——其结果当然是“意义的空洞化”。必须指出,卓越、优秀的现当代音乐作品无论具有怎样“先锋”的语言和技术探索,它们却无一例外都是以坚实、尖锐而直指人心的人性内容作为基底,否则音乐语言和风格的探索就失去了艺术的本色。不妨随手举例——匈牙利的巴托克吸收东欧民间音乐养料为艺术音乐注入强心剂,但支撑这些语言创新的基石却是这位作曲家独特的生命感受:野性、神秘,紧张的异域风情中蕴含极富个人感的表现主义。他的“夜乐”创造了前所未闻的音乐表现范畴,虽无任何浪漫主义“夜曲”的主观抒情性,但却写出了自然之夜的不可捉摸和深不可测……笔者一直固执地认为,在艺术中,“写什么”永远比“如何写”更重要,“内容”比“形式”更具根本性,“立意”比“实现”更有实质性——虽然这个美学立场在当前看来未免保守,而且这两方范畴之间的关系在具体艺术作品中会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局面,但既然当前的音乐生态已经面临危机,或许更需要我们回到艺术的根本才能看清问题。
其二,涉及接受者和社会机制层面。听众,尤其是中国听众,在面对现当代音乐时需要更多的文化准备和历史积淀。有人认为,现当代音乐更加诉诸感官和感性,所以不妨即以完全的直觉来迎接现当代音乐的奇特音响和试验。甚至曾有音乐家认为,没有以往音乐经验的“本真”听者接受现当代音乐会更容易,因为他(她)们的耳朵不带任何偏见,没有受到“污染”。我对此表示严重怀疑。在笔者看来,没有历史文脉和毫无文化准备的聆听,在面对任何音乐时都会遭遇障碍,而在面对现当代音乐时困难不会较小,只会更大——这已是当前音乐生态不断证明的一个事实。如何改善?当然是耐心而到位的教育和引导。而且,与我在上文所述的观点相呼应,在教育和引导听众面对现当代音乐(实际上是一切音乐)时,出发点应该是音乐的表达内涵,而不是音乐的语言技法,尽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现当代音乐有其不同于以前音乐的表现内涵和独特命题,它虽然可能不是很“悦耳”,不是很“中听”,但它因为体现和展示了人性和世界前所未见的侧面与层面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而这些价值意义因其产生的时间空间离我们当前的生命体验更近,因而从理论上说应该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具有更强的关联。(遗憾的是,不够卓越的现当代作品往往让人感到隔阂,反而不如十八九世纪的经典作品让人更觉亲近。)
就中国现当代音乐的社会生存机制而论,笔者以为当前一个应该引发各方关注的重要问题是缺乏“经典化”的构建和推动。所谓“经典化”,即是让真正卓越的杰作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成为众所周知的“经典”,从而使这些“经典”成为音乐生活的指路标杆并成为社会音乐意识的价值准绳。西方音乐的“经典化”过程作为“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19世纪中叶以来的建构在20世纪中得到了彻底巩固。(但也应该指出,西方音乐的“经典化”建构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保留曲目的“固化”和“保守化”,这本身也是造成现当代音乐生态出现危机的原因之一。)显然,中国音乐的“经典化”进程尚不完善,一些在业界已有口碑的优秀作品的“复演率”过低,从而导致音乐的成果积累和成就积淀未能形成社会共识。看来,我们需要各方的协同,其中包括演出季制度的设定,演出曲目中包含中国作品的惯例形成,以及理论、研究、批评和媒体机制的共同推动,等等。与此相应,我们应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中国观众领略和理解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现当代音乐中的典范作品和经典曲目——这是推动中国现当代音乐“经典化”建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准备。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152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1520号